我與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》(上)
文/曲歌
在我的寫作生涯中���,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》與我結(jié)下了深厚的情緣,留下了不少值得回味的故事……
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》復(fù)刊20周年感言
眨眼間�����,寶雞日?qǐng)?bào)20歲了���,在這張報(bào)紙20歲的時(shí)候�����,我的確應(yīng)該為她祝福�����。有句話說(shuō)����,愛(ài)是不能忘記的�,每每聯(lián)想起我與寶雞日?qǐng)?bào)的情結(jié)�����,我就很容易想起這句話�。我敢說(shuō),在寶雞凡是爬方格上癮的人����,大約都和寶雞日?qǐng)?bào)有著或多或少的聯(lián)系����,像我這種幾天不寫就心慌、手癢的人���,就更與寶雞日?qǐng)?bào)熱戀得難舍難分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?梢哉f(shuō)我在文學(xué)與新聞上的每點(diǎn)兒長(zhǎng)進(jìn),總少不了寶雞日?qǐng)?bào)眾多朋友們的扶持����。
記得最初���,我熱衷文學(xué)����,動(dòng)不動(dòng)就寫點(diǎn)兒丑詩(shī)�、散文之類,一心想發(fā)表���,而大報(bào)大刊又不敢奢望�,就想到寶雞日?qǐng)?bào)���,雖然對(duì)報(bào)社辦副刊的編輯久聞其名�,卻并未深交����,頭次進(jìn)報(bào)社,真象做賊一樣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�,緊張得未見(jiàn)編輯就冒起一身虛汗。假若當(dāng)時(shí)遇到一個(gè)冷臉漢子����,恐怕我這輩子就打消了進(jìn)報(bào)社的念頭了��。不料見(jiàn)了編輯��,卻是那樣的熱情�����,使我一下子回歸了原形���,與編輯談起了文章的得失,交流起各自的看法�����。加之那時(shí)�,我是個(gè)開(kāi)車的司機(jī),經(jīng)常往返寶雞�,我便成了報(bào)社的常客�����,除了給副刊寫稿���,也寫些新聞稿,慢慢地�����,不僅交了不少的編輯��,而且與報(bào)社的幾位老總和部主任也多有文稿之交���。
后來(lái)���,我改行辦企業(yè)報(bào),而后又在縣新聞單位當(dāng)編采�����,就更與報(bào)社如膠似漆地交往起來(lái)��。報(bào)社的朋友包括老總到縣上采訪���,多邀我陪同�,常常還給我交一些采訪寫稿的任務(wù)��,使我更有了學(xué)習(xí)寫稿的機(jī)會(huì)���。我常為報(bào)社編輯為我改的標(biāo)題叫絕��,為我的文章增色而感動(dòng)���。
漸漸地�,我與報(bào)社的朋友就像一家人一樣的親近��,有些朋友盡管在報(bào)社為官�����,但我們之間相見(jiàn)或書(shū)信往來(lái)卻互稱兄長(zhǎng)或直呼其名,相互之間直論欄目之短長(zhǎng)��,文章之優(yōu)劣�,報(bào)社的不少會(huì)議��,也邀我參加��,常被點(diǎn)名道姓讓我說(shuō)話����。報(bào)紙創(chuàng)辦《生活特刊》時(shí),還聘請(qǐng)我作了特約撰稿人�����。更使我感動(dòng)的是�, 20年中,報(bào)社對(duì)我那么多的厚愛(ài)����,甚至將我的報(bào)道推薦到陜西新聞獎(jiǎng)和全國(guó)地市報(bào)新聞獎(jiǎng)參與評(píng)選。
就這樣��,我與寶雞日?qǐng)?bào)日復(fù)一日��、年復(fù)一年地越交越深,愈交愈親�。我的“文癮” 也越來(lái)越大�����,竟大著膽子向省級(jí)和國(guó)家級(jí)大報(bào)大刊乃至人民日?qǐng)?bào)海外版寫稿和發(fā)表文學(xué)���、新聞作品�,參加各種征文���,進(jìn)而斗膽著書(shū)立說(shuō)���。盡管如今許多人追求“時(shí)尚” ,以逍遙自在和金錢為樂(lè)趣��,我等卻終日為寫作煎熬得晝夜難眠�,茶飯無(wú)味��,失去了太多的天倫之樂(lè)��。一肩挑著崗位任務(wù)�,一肩挑起新聞和文學(xué),終日疲于奔命�����,但我等卻有我等之樂(lè)�����,那就是以一種對(duì)社會(huì)的責(zé)任感而思索�����、而盡職�、而下苦����。
盡管如今,歲月使我逝去了青春���,皺紋和白發(fā)爬上了我的臉龐���、雙鬢和頭頂,但當(dāng)我品味著厚厚的剪報(bào)�����,聞著我?guī)妆疚募那逑?����,回想起?bào)社編輯乃至幾位老總為我文章所費(fèi)的心血���,以及從我發(fā)表的作品中尋覓自己走過(guò)的足跡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我為自己的奮斗無(wú)怨無(wú)悔��。因?yàn)?����,我畢竟在為我所追求的事業(yè)努力過(guò),我和報(bào)社朋友們?yōu)橹冻龅氖聵I(yè)是神圣而有價(jià)值的����。(原載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通訊》2003年寶雞日?qǐng)?bào)復(fù)刊20周年?��??/span>
我與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》的“第一次”
春日里�����,也許是人的思緒勃發(fā)的季節(jié)����,每當(dāng)有了一丁點(diǎn)兒的閑暇,我便不由得拿來(lái)我裝訂的自己在各種報(bào)刊發(fā)表的作品剪集作一番瀏覽�����。自然���,在這幾本剪集中,寶雞日?qǐng)?bào)上發(fā)表的東西最多����,其中有詩(shī)歌、散文��、報(bào)告文學(xué)����,通訊和消息�����,篇幅大到七八千字,小到“豆腐塊”�。
有人說(shuō),報(bào)上的東西都是易碎品�����,過(guò)去幾天就會(huì)被人遺忘����,而對(duì)我這個(gè)幾乎讓寫作與生命同行相伴的人來(lái)說(shuō),雖然一篇愚拙之作已過(guò)去了幾十個(gè)春秋���,可我仍然覺(jué)得它是那樣的親切,發(fā)生在文章背后的一些往事仍記憶猶新���。正當(dāng)我動(dòng)著將這些記憶作個(gè)小結(jié)的心思的當(dāng)兒�����,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通訊》的編輯約我寫一篇文章��。這倒使我覺(jué)得要寫的東西實(shí)在是太多了����,到底該從哪里起筆呢�?幾日為此而坐臥不寧后,我索性選定了這個(gè)題目����。
我發(fā)表在當(dāng)時(shí)還叫《寶雞報(bào)》的第一篇作品�����,是一首題目叫《給妻子的信》的詩(shī)�����。記得當(dāng)時(shí)報(bào)紙叫寶雞報(bào)�����,是1985年元旦復(fù)刊的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我雖然是個(gè)狂熱的“文學(xué)青年”,并在幾家不起眼的報(bào)刊發(fā)表了幾篇作品��,但對(duì)報(bào)社總有一種仰視的心理�,直到寶雞報(bào)復(fù)刊一年后才投去了這首詩(shī)�,可不到半月的1986年元月16日,這首詩(shī)居然出現(xiàn)在報(bào)紙的文藝副刊版上�。當(dāng)時(shí),我還是一家省屬企業(yè)的工人����。在當(dāng)時(shí)文學(xué)被眾多的人視為神圣的環(huán)境下,這首詩(shī)的發(fā)表�����,自然在廠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����,一伙狂熱的文學(xué)迷們紛紛找我表示祝賀���,廠領(lǐng)導(dǎo)也對(duì)我這個(gè)廠車隊(duì)的汽車司機(jī)刮目相看�,并在當(dāng)年讓我改行當(dāng)了廠報(bào)的創(chuàng)辦者和主筆����。
寶雞報(bào)大約是1988年改為日?qǐng)?bào)的���,這年春天,我成為鳳縣廣播站的“小記者��。10月31日�����,報(bào)紙?jiān)履┌嫔嫌职l(fā)表了我在這張報(bào)紙上的第一篇散文。那大約是當(dāng)年10月上旬的一天�����,我到全縣最邊遠(yuǎn)的瓦房壩鄉(xiāng)下鄉(xiāng)�,坐班車到鄉(xiāng)政府,一位副書(shū)記陪我步行到一個(gè)叫田壩子的村上����。一路之上,山地清澈的溪流���,漫處的綠色��,滿山鳴叫的飛鳥(niǎo)和山間的奇峰怪石����,使人如入仙境����;而這次下鄉(xiāng),又使我頭一次目睹了鳳縣山里人制作洋芋攪團(tuán)的全過(guò)程���,并在與村民共同享用洋芋攪團(tuán)中體味到了山地人的淳樸好客之風(fēng)�����。下鄉(xiāng)歸來(lái)��,我便一氣呵就了不足千字的散文《山趣》�,文章發(fā)表后�,報(bào)社編輯還打來(lái)電話,對(duì)這篇散文給予好評(píng)����。
正是由于這篇散文的成功和好評(píng)使我文心萌動(dòng)�����, 1989年8月寶雞日?qǐng)?bào)月末版和9月18日的專版上,接連發(fā)表了我的《山地奇物》《山地奇觀》兩篇散文�。當(dāng)時(shí)負(fù)責(zé)月末版的編輯邵文海特意給我打來(lái)電話,說(shuō)起他面對(duì)這兩篇散文遇到的一場(chǎng)“虛驚”����。他說(shuō),在他已編發(fā)了《山地奇物》之后����,又猛然發(fā)現(xiàn)《山地奇觀》的報(bào)樣���,還以為我是玩了“一女兩嫁”,但仔細(xì)一讀��,才發(fā)現(xiàn)并非如此����。通話中,這位文兄還識(shí)破了我想搞“山地系列” 的一個(gè)“暗謀”�。
1990年2月21日,《大散關(guān)》副刊頭條發(fā)表的《有位鄉(xiāng)書(shū)記》�����,則成為我在寶雞日?qǐng)?bào)上發(fā)表的第一篇報(bào)告文學(xué),也是我從事新新聞工作以來(lái)僅有的一篇以文學(xué)形式反映鄉(xiāng)鎮(zhèn)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的作品���。記得那時(shí),我極富欲望地想了解更多的縣情�����,加之總渴望掌握鳳縣這塊山地更多的素材�,以豐富我的文學(xué)積累,又極想在發(fā)行頻率較高的報(bào)紙上多發(fā)表一些帶有文學(xué)色彩的作品�。
我調(diào)到鳳縣不久,一位在縣農(nóng)工部工作的“鳳縣通” 多次告訴我���,有位鄉(xiāng)書(shū)記不錯(cuò)�,你不妨以他為素材���,寫一篇可以入書(shū)的東西。于是1989年秋���,我便趕到從邊遠(yuǎn)的坪坎鄉(xiāng)調(diào)到紅光鄉(xiāng)任鄉(xiāng)書(shū)記的這位干部�����。也真是應(yīng)了“有心栽花花不開(kāi)”那句話�����,一些人一遇正經(jīng)八百的采訪�����,便拘謹(jǐn)起來(lái)���,凈是些官話���、套話和講一些被認(rèn)為能擺到桌面上的事�,害得我盡管是絞盡腦汁�����,卻是白白“點(diǎn)燈熬油”了數(shù)日��。于是,我索性改換了思路和方法���。
一日��,借這位鄉(xiāng)書(shū)記到縣上開(kāi)會(huì)的間隙�,我便叫他來(lái)到我的“虛谷齋”喝茶 “諞傳”��, 彼此皆無(wú)避諱地聊起來(lái)����。無(wú)意間說(shuō)到在深山基層當(dāng)“官” 的苦衷����,聊一些看似擺不上“臺(tái)面” 的軼聞趣事,而這些卻撩撥得我的文心頓發(fā)�。送走了這位鄉(xiāng)書(shū)記,我便很順手地寫了這篇約2000字的報(bào)告文學(xué)��。文章投到報(bào)社不久�,稿子又被報(bào)社掛號(hào)寄回,還附有編輯的信���。認(rèn)為稿子不錯(cuò)�,本準(zhǔn)備當(dāng)期在副刊發(fā)表���,可審稿時(shí)被打回�����,原因是寫這個(gè)級(jí)別干部的稿件���,僅蓋廣播站公章不行,如能經(jīng)縣委辦或組織部同意并蓋上公章后寄回則可發(fā)表��。于是����,我遵囑將稿子及報(bào)社編輯的信送縣委組織部,并順利通過(guò)和蓋了章����。至今,每每看到這篇文章的剪樣�����,我就會(huì)想到當(dāng)年的采訪為我積累的經(jīng)驗(yàn),我還常常翻出那封編輯來(lái)信,不免生出種種感悟�����。
并非謙虛之詞�����,我不過(guò)是一個(gè)眾多“文學(xué)馬拉松” 參與者中的陪練者的角色���,也不敢在人前張揚(yáng)自己是個(gè)什么“家”����。 雖然寶雞日?qǐng)?bào)發(fā)表的我的作品中�����,詩(shī)作是最早的��,一年后�,我還在寶雞日?qǐng)?bào)發(fā)表了一首小敘事詩(shī)�����,之后,我便羞于給寶雞日?qǐng)?bào)投寄詩(shī)稿���,自然也不再在詩(shī)歌寫作隊(duì)伍中濫竽充數(shù)�����。雖然在此之前����,我曾先后在幾家小報(bào)上發(fā)表過(guò)幾十首詩(shī)�����,但通過(guò)與眾多文友的對(duì)比�����,我便自慚形穢地退出����。
但我對(duì)文學(xué)的崇拜著迷依舊�����,并于1991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、報(bào)告文學(xué)集��,也是我獻(xiàn)給山地鳳縣的第一本書(shū)——《山地風(fēng)流》���。其中就收入了寶雞日?qǐng)?bào)發(fā)表的那幾篇散文和報(bào)告文學(xué)作品。之后的日子���,我在寶雞日?qǐng)?bào)上又稀稀拉拉地發(fā)表了一些算作文學(xué)的文章����。所以����,每當(dāng)我回憶起自己的文學(xué)之路�����,總忘不了寶雞日?qǐng)?bào)對(duì)我的扶持�����;忘不了伴隨那些文章的許多美好的往事�����;忘不了那段曾經(jīng)的歷史。
說(shuō)起新聞寫作上我與寶雞日?qǐng)?bào)的“第一次”更多���。我是1988年2月調(diào)入鳳縣廣播站(內(nèi)稱鳳縣廣播電視局編播股)正式從事新聞工作���,6月11日,寶雞日?qǐng)?bào)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我寫的消息《省����、市、縣處處大開(kāi)綠燈一份報(bào)告8天就有著落》����,似乎為我的新聞職業(yè)生涯作了刻意鋪墊����,也是我在寶雞日?qǐng)?bào)發(fā)表的第一個(gè)頭版頭條新聞。這則消息反映的是鳳縣一家企業(yè)在原料發(fā)生危機(jī)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僅8天就在省、市���、縣相關(guān)部門的關(guān)心下得到解決���,這在當(dāng)時(shí)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還沒(méi)有形成的背景下,是十分罕見(jiàn)的事�����,此稿發(fā)表后����,引起了積極反響�。
說(shuō)句心里話�,至今,許多基層通訊員經(jīng)常念叨當(dāng)年寶雞日?qǐng)?bào)那張貼近基層����、貼近通訊員的“平民面孔”, 津津樂(lè)道報(bào)社慧眼識(shí)珠�,讓基層和通訊員在報(bào)紙顯著位置“露臉” 的大度作風(fēng),我也幾乎每年都在寶雞日?qǐng)?bào)頭版頭條上見(jiàn)稿����,而且上頭版頭條的新聞總能在基層產(chǎn)生“一石激起千層浪” 的效應(yīng)�,同時(shí)激勵(lì)更多基層和通訊員不惜花費(fèi)代價(jià)寫好稿����,也使報(bào)紙被基層廣大干部群眾和通訊員看成自己的報(bào)紙�。我想,這種辦報(bào)傳統(tǒng)至今仍未過(guò)時(shí)����、但愿現(xiàn)在的寶雞日?qǐng)?bào)還能保持那種貼近基層、貼近群眾和通訊員的傳統(tǒng)����,多給基層和群眾讓出一點(diǎn)版面,多給通訊員好稿一點(diǎn)位置����,從而拉近報(bào)紙與基層的距離,成為各級(jí)黨政和基層廣大干部群眾及通訊員最搶眼的品牌���,多出一些讓人們難以忘懷的好新聞和好標(biāo)題���。
可以說(shuō)在我與寶雞日?qǐng)?bào)20多年的交往中,發(fā)表最多的是消息,除了為數(shù)不多的頭版頭條����,絕大多數(shù)是巴掌大小的“豆腐塊”。這是報(bào)紙的性質(zhì)所決定的��,難怪報(bào)社的朋友常用“新聞不過(guò)千����,過(guò)千找總編” 的話提醒我們基層通訊員要多寫新、短����、活的新聞��?���?墒窃趲资甑膶懜迳闹?��,寶雞日?qǐng)?bào)卻多給我以厚愛(ài)����,時(shí)不時(shí)發(fā)表我的長(zhǎng)稿。其中有宣揚(yáng)為撲滅山林火災(zāi)�,身先士卒英勇獻(xiàn)身的原鳳縣平坎鄉(xiāng)黨委書(shū)記兼鄉(xiāng)長(zhǎng)的田建國(guó)及其在鳳縣產(chǎn)生積極效應(yīng)的《振奮人心的“田建國(guó)現(xiàn)象"》;近八千字的記敘為群眾致富鞠躬盡瘁�����,死而后已的原鳳縣黃牛鋪鎮(zhèn)北星村支書(shū)張德貴事跡的《一個(gè)村支書(shū)的不朽人生》和不少反映鳳縣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發(fā)展的長(zhǎng)篇通訊及法制紀(jì)實(shí)等方面的作品���。
而作為寶雞日?qǐng)?bào)第一次發(fā)表我寫的通訊,則數(shù)1989年10月14日二版的《一個(gè)充滿希望的工程》���、這是我對(duì)當(dāng)時(shí)鳳縣依托地域優(yōu)勢(shì)��,引導(dǎo)群眾發(fā)展甜椒的一篇追蹤性通訊����,此稿原文2000余字��,經(jīng)編輯盧國(guó)朝的精心斧正后��,以1500余字的篇幅發(fā)表��,其中可見(jiàn)這位編輯的功力和良苦用心��,也為我以后寫稿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(jīng)驗(yàn)。此外��,令我難忘的是該文發(fā)表時(shí)��,將作者名字中的“革” 字誤印成了“蘋字” ����,為此��,報(bào)上還于10月17日在報(bào)縫中作了更正并致歉���。
我的寫作生涯中���,參加各種征文�,曾被我作為檢驗(yàn)自己水平的一種方式,自然也有幸運(yùn)入選的時(shí)候��。在寶雞日?qǐng)?bào)我到底獲得過(guò)多少次征文獎(jiǎng)�,連我自己也說(shuō)不清數(shù)目,但我卻清楚����,我第一次得征文獎(jiǎng)是1993年我寫的小消息《農(nóng)民“張萬(wàn)能”真能》���,在報(bào)社舉辦的“科技致富奔小康” 征文中獲得三等獎(jiǎng),盡管這是一篇“小不點(diǎn)”�, 等次也不起眼,可我卻對(duì)其格外珍視�,因?yàn)樗吘故俏遗c寶雞日?qǐng)?bào)的又一個(gè)“第一次” 啊?�。ㄔd《寶雞日?qǐng)?bào)通訊》2007年第5——6期)

作者近照
作者簡(jiǎn)介:曲歌�,本名張革風(fēng),長(zhǎng)期從事新聞工作���,原為鳳縣廣播電視臺(tái)主任編輯����。上世紀(jì)九十年代公開(kāi)發(fā)表文學(xué)作品���,曾獲陜西省首屆兒童文學(xué)優(yōu)秀獎(jiǎng)及多種征文獎(jiǎng)���、作品散見(jiàn)于人民日?qǐng)?bào)海外版���、文藝報(bào)等中省市報(bào)刊�����,入選新華出版社���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��、作家出版社等出版的文集����,及陜西省文聯(lián)《陜西百年文藝經(jīng)典》等����。著有散文集《山地風(fēng)流》,童話集《少年奇遇記》���,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《山地子孫》��,散文集《鳳州漫記》,《五十年追夢(mèng)》����,為中國(guó)作家協(xié)會(huì)會(huì)員;在中省市媒體發(fā)表各類新聞作品萬(wàn)余篇。先后獲得中國(guó)地市報(bào)新聞獎(jiǎng)一��、二等獎(jiǎng)����、攝影銅獎(jiǎng),陜西新聞獎(jiǎng)好標(biāo)題;中國(guó)世紀(jì)大采風(fēng)征文金獎(jiǎng)����、銀獎(jiǎng)等,并被授予“金獎(jiǎng)作家”����、“全國(guó)百佳新聞文化工作者”稱號(hào);先后被授予“寶雞市優(yōu)秀記者”�����、“寶雞市優(yōu)秀退伍軍人”等稱號(hào);退休后獲“寶雞市最美老人”��、“全省離退休干部先進(jìn)個(gè)人”�、“寶雞市社會(huì)組織優(yōu)秀共產(chǎn)黨員”、“寶雞市最美五老”等稱號(hào)��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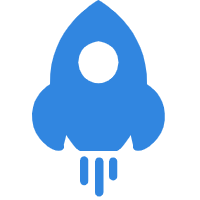 18分钟处破之好疼高清视频,大屁股夹得好紧 好爽视频里,亚洲一区激情中文字幕,92午夜福利少妇系列,一本色综合网久久,亚洲色婷婷免费视频高清在线观看,精品视频一区二区,亚洲一区二区三区 在线播放,成人3DH动漫在线播放,AV一区网站,欧美天天摸天天爽网,中文字幕mm,国产V亚洲V天堂A在线观看20,性欧美8处一14处破,heyzo高清中文字幕在线,国产V亚洲V天堂A在线观看20,亚洲网址WWW呦女
18分钟处破之好疼高清视频,大屁股夹得好紧 好爽视频里,亚洲一区激情中文字幕,92午夜福利少妇系列,一本色综合网久久,亚洲色婷婷免费视频高清在线观看,精品视频一区二区,亚洲一区二区三区 在线播放,成人3DH动漫在线播放,AV一区网站,欧美天天摸天天爽网,中文字幕mm,国产V亚洲V天堂A在线观看20,性欧美8处一14处破,heyzo高清中文字幕在线,国产V亚洲V天堂A在线观看20,亚洲网址WWW呦女